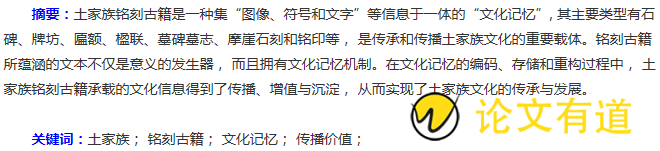
土家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铭刻类古籍资料。这些珍贵的铭刻类古籍资料是土家族古籍资源中的一枝奇葩, 也是我国古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后世研究土家族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极具资料价值和实践价值。为了实现土家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弘扬, 对土家族铭刻古籍所蕴涵的文化记忆及其现实价值进行挖掘和研究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土家族“铭刻古籍”概况
土家族虽然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 但由于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字, 因而, 土家族的“古籍”一般是用汉文记载的, 一般划分为“文字类”与“非文字类”两大基本类型。土家族铭刻类古籍为文字类, 按其形制主要有石碑、牌坊、匾额、楹联、墓碑墓志、摩崖石刻和铭印等类型, 其中以石碑、墓碑墓志与摩崖石刻居多, 仅就《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 (土家族卷) 中收录的铭刻古籍来说, 就有二百八十余通石碑、一百余通墓碑、三十余合墓志及二十多处摩崖石刻。土家族铭刻类古籍涉及的范围广泛, 内涵丰富。后晋天福五年 (940) 十二月天策府学士并任江南诸道都统的李弘皋撰文, 天策府都慰、抚风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马希广铸“溪州铜柱”铭文, 记楚王马希范与溪州刺史彭世愁的交战议和与“订立同盟事”;宋嘉佑三年 (1058) 殿中丞、充辰、澧、鼎州体量公事雷简夫撰文, 大理寺丞、辰州签通判、掌视密甄升抄刻的明溪新寨题名记摩崖石刻记辰州与溪州攻伐并议和事, 展示了土司与官军交战议和到订立盟约的历史事实;同时, 彭荩臣华表联墓联是于明嘉靖三十五年 (1556) 在现今湖南保靖县迁陵风筝坪立的, 记保靖土司彭荩臣带领一万余名土兵奔赴东南沿海抗倭之王江泾一役, 斩杀敌人三千余首, 使明朝海疆转危为安, 史称“东南战功第一”;明万历四十二年 (1614) 在贵州沿河洪渡立了“军门禁约碑”, 记明代地方政府发布的关于禁止“汉人入夷”和“勾引夷人入汉”而引起事端要受到处罚的告示;还有明崇祯二年 (1629) 为纪念明崇祯皇帝对湖广容美土司田楚产授爵士和褒奖而于湖北鹤峰立的“奉天诰命碑”;再如现恩施城郊七里坪旧州城 (即南宋时期的施州清江郡郡治所在地) 的南宋咸淳六年 (1270) 秦伯玉所撰摩崖石刻, 铭记南宋咸淳年间恩施种植西瓜的情况;清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在来凤百福司立记卯油行的“卯洞油行碑”, 清嘉庆初年在贵州思南鹦鹉大头坡桶井管理乌江航运的石碑等。[1]
土家族铭刻古籍不仅形制多种多样, 庄严稳健、造型精美、工艺精湛, 其铭文内容也十分丰富, 涉及范围极广泛, 它涉及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政治与军事、教育与文化、经济 (农业) 发展与家族源流、宗教与信仰、制度与规约、道路与交通、疆域地界, 还有很多称颂表彰类的。根据铭文内容可划分为“祭祀碑与纪功碑”“纪事碑与告示碑”“标示碑与政训碑”等, 蕴涵着社会与文化、生态与经济等现实价值, 为土家族的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军事、交通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土家族铭刻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凝固成的土家族人特有记忆。这些土家族铭刻古籍所承载的文本信息反映了土家人民对神灵的敬仰和对祖先的敬奉以及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示着土家族社会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脉络, 潜移默化地传承着土家族文化及其精神。
二、土家族铭刻古籍的文化记忆表达
铭刻古籍是文化传承和传播的重要载体, 它所蕴涵的文本是文化记忆的一种重要形式。苏联着名学者洛特曼认为“文本是以特殊形式构成的、能够包括大量浓缩信息的综合体”[2];语言学家康德·埃希里则指出“文本”是指“再次接收的消息”.可见, 文本的“元形式”不是被评注的原始作品本身, 而是从中传达出的相关“信息”, 其明显的特征就是“再次接收”[3].基于时序更替和社会发展, 关于文本的研究和认识逐步深入, 认为文本主要指的是“完整意义和完整功能的携带者”[4].通常认为, 文本的完整功能主要有“信息的传递”“信息的生成和信息的记忆”等三种, “记忆功能”是其中之一。由此可知, 土家族铭刻古籍是历史积淀的产物, 它们是集图像、符号和文字交流信息的人化世界的实物形态, 具有意义, 它既是一种空间, 更是一种存在, 有着自身的惯性和持久性, 更是无法轻易地被消融的意义感知。土家族铭刻古籍不仅是具有完整意义的携带者, 而且还拥有保存自己过去语境的能力, 这种能力就是其记忆携带, 它既是一种直观形象的物化空间性记忆表达, 也是一种蕴涵特定文化意义的符号记忆表达, 还是该地域社会发展变化的实践性表达。
(一) 土家族铭刻古籍的空间性表达
“空间性文本记忆”是指基于土家族铭刻古籍的文本本身空间的一种物化形态, 它有着其自身内部所固有的组织结构, 意味着接受者对其物化形态上的承认和理解, 是一个留给后世认同和理解的承载着具有载体材料与外观形象、地理空间与特有区域等物理性的空间记忆, 如溪州铜柱展现的地理空间性文本信息是:行政区划“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王村”, 铜柱的高度是400cm, 入地200cm, 直径39cm, 其形状为八边形, 每方宽15cm, 重2500kg, 中空内实钜钱, 柱上端覆盖铜顶;八面有字, 每面199×15cm, 面刻180×15cm, 每面5至7行不等, 八面所刻25行, 计2000余颜、柳阴文。其铸立的直接原因虽是会盟誓守, 从其“柱”形外观上看, 它承载的文本记忆不仅仅是“铜柱”的高大、威武、壮观和厚重等直观印记。值得深思的是, 溪州铜柱还是西南少数民族特有风俗习惯的一种反映, 既是当地少数民族普遍接受的一种盟誓形式, 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要盟或诅盟”制度。[5]可见, 铜柱铭文的字体、格式、体例、字数都是铜柱物化了的空间性文本记忆。再如, 建于明天启年间的唐崖土司牌坊, 也可看作一个整体性文本。牌坊所承载的空间性文本记忆主要有:牌坊位于唐崖土司城的“正中央”, 前临街、后靠衙院, 是唐崖土司城遗址所在地的中心。牌坊是唐崖土司城的“镇城之宝”, 是其地理空间性记忆的一种展现;牌坊四柱三门, 亭阁式, 全石仿木结构, 檐为翘角, 收方自然, 呈现出整齐、庄重、威严的艺术效果, 展示了其较好的结构空间性文本记忆。
(二) 土家族铭刻古籍的符号性表达
现代符号学理论认为, 符号是一个根据“能指”与“所指”所构成并按照“符码”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6], 它积极倡导运用符号的观点来解释并研究社会现象---“能指”指的是按照“物质和行为或表象载体”融合所形成的具有特定符号意义的总称, 是符号意义中可以被感知的部分, 又叫“意符”;“所指”是通过某种符号性载体来表达的文化意义, 即思想与象征性等, 指的是“能指”所指向的某种东西;“符码”则指的是符号性“表意活动”中应遵循的相应规则。这样看来, 一方面土家族铭刻古籍是保存土家族文化记忆的特殊符号, 是历史存留下来的、表达着特定意义、具有稳定性和特定内容的客体;另一方面, 土家族古铭刻又是行为与实践的场地, 是记忆的载体, 是记忆的另一种形式---被记忆。土家族古铭刻是记忆的某种“场”, 是一个由“能指”“符码”“所指”三要素所构成的特定文化意义的符号系统。因此, 土家族铭刻古籍所表征的是具有特殊表意的符号系统。它虽然本身并不会记忆, 但作为特殊的符号主体和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 能够通过隐藏在其中的表意符号来唤起共同的回忆, 使人们感知民族的历史、触摸先祖的过去。明熹宗天启三年 (1623) 修建的唐崖土司牌坊, 不是随便可以建造的, 通常需要得到官方的许可, 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唐崖土司牌坊是明熹宗为表彰覃鼎的武艺和军功而建造的, 体现出官方对覃鼎的充分褒扬和肯定。牌坊中门坊额下用象鼻石雕加以装饰, 集人、物、文字、书画于一体, 布局别致。这些图案、文字、书画在牌坊的整体结构分割比例、大小、建筑材质要求、艺术风格等符码的规定下, 组合排列形成特定古建筑物及其群落。整个牌坊在其建制上既具有汉制特征, 又凸显出土家族的文化特色, 如牌坊中的“土王出巡”就是直接的土司社会生活记忆;牌坊中的“麒麟奔天”图案, 是吉祥文化象征, 而“舜耕南山”图则体现出土家族人“崇尚孝文化以及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继承”[7].整个牌坊, 无论是其建筑物的外在结构, 还是它所承载的意义均可看作是中原汉文化与本土人文艺术融合的符号文本记忆。在土家族古铭刻中, 承载着许多构图立意极为巧妙的图像、文字, 它们都具有特别的符号意义, 都是土家族古碑刻符号文本记忆的表征。以利川市鱼木寨的墓碑群为例来进一步说明。调查显示, 鱼木寨现存墓碑大多为墓主人生前所修的“生基碑”---墓主人生前就为自己修好的墓碑, 这些墓碑雕刻于明朝末期。寨中仅“碑屋” (即埋藏于住宅里的坟墓) 就有10余处, 现有9座比较大型的墓碑保存完好, 其造型奇特罕见, 如成永高夫妇的墓碑, 外型呈“左右侧三门, 二个院落”样态, 非常雄伟壮观。值得注意的是, 鱼木寨中常见的墓碑雕刻图案主要有龙凤、人物、山水、花鸟及草虫等。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双寿居”为例, 三进墓, 每进均为雕刻石门, 墓碑上刻有36折戏曲故事, 500多个人物, 碑角双龙口含珠, 珠可滚动, 文字字体八体俱全, 其雕刻工整豪放, 有学者称其为石雕艺术之集大成者。一方面, 这些雕琢蕴含着土家人浓烈的“驱鬼”“避邪”“吉祥”“仁孝”等美好愿景及对装饰艺术的向往与追求, 另一方面还是“权势与荣耀、圣明与贤德的象征”[8].
(三) 土家族铭刻古籍的实践性表达
土家族铭刻古籍是土家族地区人们社会生活实际的客观表达, 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首先, 铭刻古籍所记载事件发生的时间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铭刻古籍产生的时代背景, 便于理解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其次, 铭刻古籍中记载的人物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国家政策和社会角色分工;再次, 铭刻古籍记载的事件评价可以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有更深刻的认识。如溪州铜柱是溪州之战化干戈为玉帛立柱盟誓之史证之物, 是彭氏与楚王结为政治同盟的标志, 成为溪州彭氏地方政权建立的基础。溪州铜柱的盟誓, 创造性地建立了溪州都誓主领导下“群酋合议制度”, 开创了我国西南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 是西南土司制度的创立者和实践者。溪州铜柱的六次迁徙, 见证了彭氏地方政权发展的历史轨迹。溪州铜柱历经沧桑, 见证了彭氏司治的开始、发展与终结, 是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历史与土司制度的实物证据, 是永顺土司遗留下来的无价之宝。[9]
三、土家族铭刻古籍的文化记忆过程
根据文化记忆理论, 文化记忆过程就是指文化的“编纂、储存与重构”过程, 是社会记忆的一种特殊的形态。编纂就是编码, 储存就是保存, 重构则是以编码和繁殖原则为基础进行的文化“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 文化、记忆和媒介相互关联, 文化通过承载文化信息的媒介将信息固定与时空型构而结晶为记忆, 记忆通过媒介传播而得以传承和发展, 媒介确保记忆的再次识别和延续。因此, 文化也正是通过其记忆过程而得以传播、发展与进步。土家族铭刻古籍表达着自身独特的文化逻辑、动力和活力, 将其置于文化记忆过程的动态选择与发展过程中, 更有利于我们分析和考察土家族铭刻在文化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的独到作用。
(一) 土家族铭刻古籍与文化记忆编码
文化记忆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识记, 展现在记忆媒介上的内容都是特定时代的主观感受以及与外界环境因素互动的综合结果。文化记忆编码就是指文化传播主体根据特定的目的与需要, 筛选信息和媒介, 最后将筛选后的信息记录在媒介上, 从而完成整个编码过程。
以土家族古碑刻为例, 土家族碑刻文化传播的主体是土家族及其碑刻媒介生产者。碑刻媒介生产者多为当时的政治与文化精英, 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土家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治理的需要。碑刻文化的传播对象既有土司及其家庭成员, 也有土家族区域的一般民众, 其内容主要涉及姓氏与源流、宗教与信仰、农业与教育、制度与公约、军事与颂扬、道路与交通、建筑与名胜等。目前发现的湖北省鹤峰县容美镇的祟祯二年御赐给容美宣抚司宣抚使田楚产的“奉天浩命碑”与明永乐年间宣恩椒园水田坝村的客家知识精英为施南宣抚司所撰的“施南土司石刻”, 是对当时土家族土司最为直接的观察与描述, 既是明代不同社会阶层多视角聚焦土家族土司的结果, 也是土司及其家庭的观念、情感与意象等客观真实的写照和还原。
可见, 在土家族碑刻古籍所承载的记忆编码, 其传播目的主要表现为政治主张的宣扬、统治思想的确立、宗族观念的延续、教化理念的传导、先祖的追思、个体意愿的表达、媒介形象的塑造等, 以达到歌功颂德、昭示后人, 以图永存, 其受众对象既有官方人员, 也有土司及其家人, 还有土家族民众及其特定的群体或组织。正是基于这些目的和需要, 传播主体选择性地记录了土家人的活动讯息, 并将这些讯息储存在碑刻媒介上, 进而逐渐传播。传播主体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其特定目标, 顺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优先选择碑刻作为媒介, 表明土家族铭刻古籍文化记忆编码中蕴涵着的内在逻辑关联因素。
(二) 土家族铭刻古籍与文化记忆存储
一般情况下, 文化记忆中的“存储”就是利用“媒介”对信息进行保存且传播, 其记忆存储能力是由媒介特质和传播特点所决定的。“媒介特质”对文化记忆“存储过程”中信息的选择、保存与传播具有内在的关键作用, “媒介特质”使“后史”成为“前史”的见证。[10]可见, 土家族铭刻古籍作为土家族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特质, 具有其特定的媒介特质和传播特点。
1. 土家族铭刻媒介具有肃穆、神圣、威严的特
质, 如给土家族带来无边患战乱达800年之久的溪州铜柱, 对于溪州来说, 可称为“定州神柱”.土家人视铜柱为神物, 哪怕是历经千年, 受众在尚未阅读其承载的文化信息前, 仍会被其威严所震慑。
2. 土家族铭刻古籍多为“石”“铜”等材料, 具有
坚固耐久、不易损毁、易于保存, 可以充分发挥时空维度的传播优势。如恩施“西瓜碑”, 就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年代最早且保存比较完好的记载恩施西瓜种植讯息的农事碑刻。该碑虽历经几百年的风雨侵蚀, 碑文风化剥落严重, 但依然是佐证我国南方引种西瓜的重要实物资料。可见, 土家族铭刻古籍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 具有时空传播优势, 既可以跨越时代传播, 也可利用现代技术处理而突破空间的限制开放传播, 这正是其历久不衰, 至今仍被土家族及其他民族学者高度重视的根本原因。
3. 土家族铭刻古籍蕴涵信息的真实性和安全系
数较高。土家族铭刻古籍是原生态文化资源, 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古碑刻与墓志铭文均是当世之作, 为时人所见证, 几乎不可能存在信息虚假的问题, 因而成为后世校订史实的可靠材料。铭刻文本在使用过程中, 转抄多为“拓印”或“拓石”, 存真无误, 更不会出现脱漏现象, 其信息与原本内容基本一致, 准确度极高。同时, 铭刻作为实物性媒介, 其刻写面积受到极大限制, 在用词上十分精练, 文字内容也言简意赅, 信息密集度高。因此, 土家族铭刻古籍作为特殊的信息存储媒介, 所保存和传播的信息精准可靠, 符合了传播主体的传播需要而成为土家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见证了土家族文化的史实。
(三) 土家族铭刻古籍与文化记忆重构
文化记忆重构是在当下文化语境下, 对媒介所承载的信息进行重新梳理, 在传统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现和回忆, 实现文化讯息的传播, 在保持民族主体文化的基础上, 吸收与融合其他民族优秀文化而使民族主体文化逐步实现自我更新的过程。民族传统文化在其重构过程中得到传承, 并在传播中不断丰富和发扬光大。
铭刻古籍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在文化记忆的重构过程中, 其传播主要方式有直接传播、拓印传播与评论传播三种。前两种传播方式更多地是完成文化记忆重构的信息提取与再现, 将铭刻所承载的各种讯息清楚、直接、具体地传播给受众;而评论传播则指那些对铭刻感兴趣的学者、文人、艺术家等, 通过他们对铭刻的评论, 发挥其影响力, 使其承载的文化信息在更多的受众群体中传播。铭刻古籍的文化受众有两种:一种是在阅读碑刻古籍后不再进行传播, 另一种是阅读后还会对的内容进行评论, 再进行二次传播。在二次传播过程中, 铭刻古籍的受众会以自己所处时代为参照框架, 对文本进行理解与重构, 将自己带入文本之中, 与文本的人物与关系发生互动, 不断进行自我审视与反思, 进而认识更深层次的自我。在受众与铭刻古籍文本的互动过程中, 铭刻古籍的文本从一个文化域越入另一个文化域, 并在两种文化域的边界为自己编码, 产生在原本语境中没有的意义。
在不同受众的作用下, 土家族铭刻古籍文本讯息实现了文化记忆的重构。在此过程中, 土家族文化讯息以土家族铭刻为载体对受众施加影响而凝结为文化记忆, 促进了人们对土家族的认识和了解, 如鱼木寨六吉堂“南阳柴夫子训子格言”碑刻表达的是天下父母望子成龙、劝学教子的教化理念愿景, 是土家人教化艺术的再现;又如向梓阎孺人之墓上有“杨香救父”是对孝文化的传承。这就是说, 从土家族的墓与碑等石刻艺术的形式与内容, 揭示了土家族人对“功德”“善事”“节操”“孝道”等的颂扬, 对“教化作用, 以达到引导后人”的追求。[11]土家族古铭刻“既是珍贵的历史实物资料, 又是土家族文化活动的重要文化符号”, 具很强的研究和审美价值, 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对它进行收录、解读、评说与传播。在文化重构过程中, 受众都是从自己的文化语境出发对文本进行审视与解读, 从而产生新的符号意义, 如学者在研究利川谋道田昌隆夫妇墓碑衬鼓上人首鳖身的图形时认为, 人首鳖身的造型不仅反映出古人的生殖崇拜, 同时也反映出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 是学者在自己所处时代语境下重新解读墓碑上的文本, 使墓碑文本产生了与时代相呼应的意义。在文化重构过程中, 一方面记忆发挥了文化讯息的存储器和发酵器的作用, 使土家族文化得到了认同, 积淀了文化讯息;另一方面, 土家族铭刻作为独特的艺术载体, 在文化教化与艺术审美方面的价值被不断放大, 即人们在获取信息的同时, 从中得到思想的启发和美的享受, 激发了文化的认同, 使得受众群体不断扩大, 传播生命不断延长, 实现了文化增殖。从受众对铭刻内容的揭示, 到对铭刻文本的解读, 以及对铭刻内容的研究与传播, 最终实现了铭刻古籍的文化记忆重构、增值与传播。重构后的文化记忆更容易获得受众的认同, 使土家族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在“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土家族铭刻古籍, 是一种原生形式古籍, 是土家族先民在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珍贵文化遗产, 是土家族社会发展的印记, 从侧面反映了土家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通过文化记忆的编码、存储和重构, 土家族文化讯息得到传承和传播。土家族铭刻古籍价值研究, 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呼唤一种主体性力量, 从而更加自觉地传承与维护”[12]土家族文化, 实现土家族内在精神与信仰的传承。因此, 对土家族铭刻类古籍及其文化记忆进行整理和探讨, 既可把握土家族发展的历史脉络, 又可传承其蕴涵的信仰崇尚, 以塑造土家族特有“文化的气质与民族的性格”[13], 对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发挥着积极作用, 也可为当今土家族的社会管理及其治理提供理性借鉴, 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3-4.
[2]康澄。文本--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J].当代外国文学, 2005 (4) .
[3] (德) 阿莱达·阿斯曼, 扬·阿斯曼。冯亚琳, 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8.
[4]彭佳。另一种文本中心--回应尤里·洛特曼的文本观[J].符号与传媒, 2011 (2) .
[5]彭剑秋。溪洲土司八百年[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
[6]张建华。符号学视域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传承[J].中国体育科技, 2015 (3) .
[7]曾超。唐崖土司牌坊的“历史性价值”述说[J].三峡论坛, 2015 (3) .
[8]谭宗派。鱼木寨研究[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17-20.
[9]雷家森。溪州铜柱的树立与迁徙考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14 (6) .
[10]汪鹏。碑刻媒介的文化记忆与传播方式--以嵩山武则天碑刻为例[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 (3) .
[11]向杨杨。土家民间石刻艺术中的教化理念浅析[J].民族艺术, 2012 (1) .
[12]王霄冰。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J].江西社会科学, 2007 (2) .
[13]蒙耀远。水族铭刻类古籍搜集整理架构述略[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