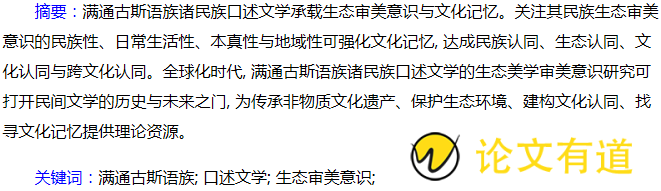
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生活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部及俄罗斯远东地区, 中国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包括满族、锡伯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及赫哲族, 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内的满语支和通古斯语支。其中满语支包括满语、锡伯语和女真语 (现在只保留于文献中) , 使用者主要分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黑龙江省黑河市与齐齐哈尔市富裕县、辽宁省沈阳市等。通古斯语支包括鄂温克语、鄂伦春与和赫哲语, 使用者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的鄂温克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及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县、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塔河县等, 使用该语支人口不足千人。[1]

生态全球化时代, 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文学在北欧、北美及中亚、东北亚地区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和研究价值。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民间文学存有口口相传的生态审美文化特点, 有无文字记载的神话、传说、史诗、故事、歌谣、谚语、谜语等文学体裁, 承载了人类对自然的亲近、敬畏和义务, 呈现了生态审美意识的系统观、联系观和整体观, 凸显了北方少数民族文学审美意识的生态文化价值。生态审美包括主体的审美意识、客体的审美意蕴及主客体的审美关系趋向生态性的统一, “主体的生态审美意识在合态审美场中初生, 为发展了的整生审美理式、共生审美范式所化育而成”[2]。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口述文学承载着本民族的生态审美意识, “对在审美实践中形成的审美形象信息, 经过贮存、加工, 在同客体对象相互作用中经过同化、顺应作用和反复的反馈, 才形成同语言密切联系, 并以语言为载体的审美意识”[3]110。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口述文学富有生态审美意识, 包括生态审美趣味、生态审美态度、生态审美理想和生态审美评价四个层面, 具有民族性、日常生活性、地域性和历史传承性特点。
一、生态审美趣味:宇宙“小我”乐生的自得其所
生态审美趣味是生态审美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现了生态审美情感、生态审美观点、生态审美能力、生态审美理想。每个民族因自然环境、语言、习俗等因素产生各自的生态审美趣味, 即休谟所谓的“趣味无可争辩”。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世代生活在北方的白山黑水间, 先民以捕鱼、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 广袤的山林河川成为其口述文学创作与传承的根源。在生命与自然的轮回中, 人们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彰显自然的崇高、供养与强势, 悲叹人类的渺小、依赖与弱势。
人类不过是生物链中的一环而已, 并不处于征服与主宰自然的制高点。民族生态审美学研究强调:“生态审美研究的中心, 应该是人的生存状态, 生命的存在状态。”[4]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生态审美趣味是生态审美意识的根基, 基于主体生态审美享受、生态审美的欲望、生态审美需求、生态审美动力不停息地变动。审美客体取决于生态性, 审美主体则处于永生、乐生状态, 两者构成生态化的审美趣味系统, 与满通古斯人的生存环境、生存习性、生存欲求、生存价值、生存目标、生存心境达成统一。
春夏秋冬轮回、山火突袭、洪水爆发、猛兽攻击, 给予北方少数民族应对残酷生存条件的生存能力, 在其口述文学中, 歌咏了终生狩猎为业的莫日根敬神、狩猎常识禁忌, 以及与动物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是不断地接近自然;文化就是指与自然的潜能 (potential) 相一致的现实 (actuality) 。”[5]生活在山林区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有山神信仰;居住在三江边的赫哲族人信仰江神、龙神。在鄂伦春族猎人们看来, 大树、老人与老虎都是山神“白纳恰”的化身。鄂温克族杜国良讲述了绰号为“大雪”的莫日根达额图氏的奇遇:“老虎已爬到顶上, 忽然闻到生人气味, 老虎背上的毛直竖起来, 狂怒地咆哮着, 甩起了尾巴。大雪莫日根大声喊叫着, 顺着山沟就跑, 老虎一下子扑到死鹿跟前, 用鼻子闻了半天。这下可把大雪莫日根救了。他出了峡谷还跑了好久, 就像是一只被狼追赶着的狍子一样。这时, 他明白了, 那只死鹿不该归他所有, ‘白纳恰’没有赐给他, 是属于老虎的。”[6]由此可见, 人类不过是自然的“小我”而已。
二、生态审美态度:万物皆神灵的各得其所
生态审美态度是人类对生态审美活动和审美对象所持的态度, 是产生、维系、发展生态审美关系的关键因素, 受制于生态审美理想与生态审美评价, 主体的生存世界不断地融入神灵, 并且参与到审美世界中, 进而形成持续的生态审美活动。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生态审美态度也许有功利, 却全然不是旁观、占有或征服, 体现的是人与生态环境各得其所的价值关系。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信仰萨满教, 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及祖先崇拜中升华为生态审美态度。萨满信仰日渐消失, 但所包含的文化记忆依稀存在, 如满族与鄂伦春族民间至今流传着《尼山萨满》[7]传说。2013年2月18日, 笔者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族民族乡调研时, 鄂伦春族人葛秀芳讲述了《尼山萨满》片段1:
有个女萨满洗头呢, 有哥俩来了, 把这个女萨满扔井里了 (这个萨满就是尼山萨满) 。这个萨满的神是天鹅 (“得义”) , 天鹅是最大的神, 女的, 跳大神的有龙、鹿, 什么都有。过去, 都是跳大神的整的, 就是神衣上扔的铃铛。过去, (萨满) 就这样来的。所以, 有病的人就让他好, 有的不是那个萨满。萨满也有小的, 也有大的。就这些了, 挺长的, 都忘了。 (张晓华:“有病什么的就找她, 也有不行的。”孟晓英:“过去, 不敢打听, 挺神秘的。”)
自然崇拜体现了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对自然万物的想象与情感, 出于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祖先崇拜思想浓厚, 至今仍广泛地体现在敬老习俗中。满族的祖先崇拜在其家祭萨满神词中清晰可见。2016年8月19—20日, 笔者在宁安市江南乡东安村的觉罗洼子富察氏萨满家祭调研, 其家族所敬拜的佛爷号分为上午神与下午神, 上午神包括白色的神、大贝子、兵将军、上面的师傅、安春香;下午神包括太阳之子、北斗、福神、贤淑的、佛爷扇子、笊篱姑姑、智慧师傅、锐力祖母、海线青、耳环妈妈和火盆。2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关扣妮说过:“灵魂是金色的。”3金色即太阳光的颜色, 成了神圣与生命的颜色, 萨满在舞动中迷失了自己, 西方的天使借助翅膀飞翔, 萨满借助的是萨满服上的飘带飞翔, 萨满服上的金属保护着萨满的生命, 上天入地进入神的世界, 即审美世界, 即如痴如醉、如梦如幻的境界, 萨满不是与神通过争斗, 而是向神请求取回病人的灵魂。“萨满就好言相求, 判官后来说:‘那就让他活到三十岁吧!’萨满说:‘三十岁哪行呢, 自己还管不了自己, 他还没有过家门呢……’判官又添了十岁, 萨满照样搬出一大堆理由来, 最后, 判官添到九十岁, 萨满才同意, 给了判官很多银子, 带着色勒古勒片郭的灵魂走了。”[8]此外, 萨满神词即是向神灵付出的代价, 甚至萨满本身也要付出同等代价交换。据鄂温克画家柳芭所言:“姥姥每救回的一条生命, 都是用自己子女的生命去换取的。”4这种万物皆有灵的观念, 不仅将灵魂安放在万物之中, 且将之安放在其生存环境中, 强调人的灵魂既不万能、也不高贵的共生的审美态度。
三、生态审美理想:亲近、依赖与敬畏自然的物我相依
生态审美理想是人类期待、憧憬与追求的至高至美境界, 与生存理想、生活理想和社会理想相融合, 生态环境美是其集中体现, 共生的审美理想上承下达地趋向生态性。生态审美理想对审美主、客体起着双向规范、同构的作用。
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族源故事讲述的多是人与动物的血缘关系, 如鄂伦春族民族起源故事涉及熊图腾, 满族民族起源故事中的神鸟崇拜等。正是人们这种对自然的亲近、依赖与敬畏的心理, 形成了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生态审美理想的初因。2016年10月4日, 笔者在街津口赫哲族风情园调研, 导游赫哲族人尤秀云用赫哲语为游客们演唱了《秋天赐福》:“天神哪, 你给我很多的孩子, 让我有很多的孩子, 再给我很多的鱼呀, 野兽呀, 让我的家人、孩子们好好地生活。天神呀, 你在我身边哪;天神呀, 我也在你身边哪, 咱们就在一起生活吧。”5这段表达生存内涵的民歌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审美内涵、生态审美理想与生态审美创造, 即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神灵所赐, 都是自然给予的。“在纯粹口语社会, 记诵和歌曲可以囊括全部人生经验, 还包括宇宙观和神学观。”[9]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依存的审美关系中, 人与神共同“诗意栖居”的生态审美理想, 与传统文化中的民众生存及生态保护智慧一脉相承。
赫哲族人吴连贵说唱的伊玛堪《木都力莫日根》, 表述了幸福且美好的生活根源于自然。“娶亲时来的说唱伊玛堪的老翁喝上几杯酒, 高兴地为新�O新娘唱起祝福歌: (唱) 嘎格伊格哪, 嘎格伊格———哪!天上的明月, ———为你们指路。天上的星星, 给你们祝福。森林里的百鸟, 为你们歌唱。江里的鱼, 为你们高兴。你们像山一样, 永远也不会老。你们像松树一样, 四季都长青!两对夫妻拜过天地、拜过灶神, 拜过祖宗三代牌位完了以后, 人们全都坐下喝起来了。”6在日常生活中赫哲族人由亲近、依赖与敬畏自然, 发展为感恩天地、感恩神灵, 延伸到感恩他人。2016年10月5日, 笔者在赫哲族聚居区调研期间, 住在76岁赫哲族老人吴桂兰家中, 为了感谢笔者带她去了北京, 老人特意做了刹生鱼、土豆炖鱼骨架与烤塔拉哈。吃饭前, 吴桂兰老人将泡好的人参酒倒入高脚杯中, 用筷子在酒中沾湿后洒向天与地, 才开始喝起酒来。7吴桂兰老人为了向治好她腿病的医生表达感恩之情, 她还坐客车去了同江, 给那名医生送去了两条大马哈鱼。可见, 生态审美理想通过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价值评估, 决定了生态审美态度和生态价值观, 构成生存活动、审美活动与创造活动“三位一体”的生态链。
四、生态审美评价:身体与情感、道德的修身教化
生态审美评价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审美价值的评估, 是人类在自然事物形式美判断基础上对自然事物内容美的审美态度, 是人类生态价值观的体现。生态审美评价关联生态责任与义务, 主体对生存价值、功利价值、认知价值的关注与选择, 决定了其审美价值的取向, 美学思想借此得以萌生。
人类为了生存, 满足自身的衣、食、住、行自然成为第一要素, 人类身体提供了生态审美器官。在满族神话《三仙女》中, 三个仙女下凡到长白山的仙池中洗澡, 第三个仙女因贪恋吃“香美可爱”的朱果而感孕留在人间, 她的生活是美好而快乐的, 在吃果受孕后, “所有的花草和树木都如此地欢欣。第三个仙女把树皮剥下来披在身上御寒, 每个季节都有天赐的衣服”[7]12。后来, 爱新觉罗的先祖诞生了, 仙女“让他顺流而下, 死了就死了、能得救就得救吧!……过了三世, 不知是谁生了老罕王, 他的姓就是第三个仙女所告诉的:‘姓觉罗, 称作爱新觉罗。你的子孙原本就是为治理国家而来的’”[7]12-13。生态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人类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 它必然超越物质的直接实用功能, 与人类的生存、持续发展及人性完善产生必然联系。例如, 在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 狠心而奸诈的嫂子到头来诸事得恶果, 憨傻而善良的弟弟总是好心得到好报, “这时节正赶上连雨天下涝雨, 大道上有不少拉绸缎的大车给泥陷住了, 怎么也拉不出来。老二看见了, 就用黄狗小巴儿帮助商人拉绸缎大车。说也怪, 眼看着黄狗小巴摇头摆尾地没费劲, 把一辆辆大车都拽出了泥坑。商人给老二不少绸缎和银钱。看老二的日子过好了, 嫂子所得直咬牙”8。此外, 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集天下之大爱, 甚至跨越了血缘关系。2016年10月3日, 笔者在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调研, 赫哲族孙玉琴老人谈及她40多岁未婚的四儿子时说:“他能娶个离婚带女孩的最好了, 我们先稀罕稀罕, 结婚以后他们再生呗。”
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口述文学传递着身体审美、诗性体验、情感表达与道德教育, 是生态审美认同的理解与对话。“它以主客体之间的同一性和主体对这种同一性的认知为基础。审美认同的对象有地特定审美对象的认同, 对他人审美评价的认同和对艺术家创造才能、创作特色的认同等……其极致是达到主客体的统一和谐、物我两忘……对美好事物的认同使人求真向善和努力发现美、创造美。对丑恶事物的认同则使人消沉、堕落。”
五、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口述文学生态审美意识的局限与价值
如果说当下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口述文学展示的不过是一种表演活动, 实则是其生态审美意识的回归而不是远离, 因为其本身就具有交流的性质。“将表演视为一种艺术性的交流模式, 即主张表演牵涉使用语言的一种方式, 一种言说方式, 这一方式对于某一特定言语共同体的成员而言, 是一种可以交利用的交流资源。”[10]只不过观看表演的观众已远离了大自然的生存环境而已。正如当年伏尔泰嘲笑卢梭要爬回原始社会的哲学思想, 现在应该嘲笑的却应该是:即使人类想要爬回原始社会去, 已然没有原始社会的生态空间可以接纳罢了。
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创造与流传的口述文学已淡出现代社会日常生活, 生态环境的被破坏更让人类反思与珍惜。语言是思想的载体, 当下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人口近千万, 然而, 其民族语言却走向濒危, 空留民族文字的无声诉说与无文字语言的文化密码, 致使其蕴含的生态审美意识难以寻根溯源。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将世代流传下来口述文学作品结合历史记忆、生态环境和民族语言, 反映了不同民族在不同社会时期的审美意识、生态文化形态和审美心理特征, 体现了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的社会风貌和精神世界。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口述文学仍有待进一步挖掘、整理与研究, 其传承性与创新性可为当代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例证和启示, 同时有助于传承与发扬民族生态审美思想和美学精神的现代价值, 进而拓宽中国生态美学史的研究思路和维度。
参考文献
[1] 季永海.满通古斯语族通论[J].满语研究, 2003, (2) .
[2] 袁鼎生.审美生态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415.
[3] 朱立元.美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4] 黄秉生, 袁鼎生.民族生态审美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7.
[5] 齐格蒙特·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85.
[6] 杜国良.莫日根趣闻轶事[M].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5:160.
[7] 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满族古神话[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7.
[8] 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 (第二集) [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262.
[9] 杰克·古迪.神话仪式口述[M].李源,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45.
[10] 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05.

